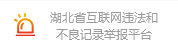■ 蔡远福
在我看来,书房就是一个读书人心目中理想的心灵栖息地和完善自我的精神家园。这抑或正是麦家“读书就是回家”之云的本原吧。
我算不得勤学之人,但从小就爱书。在山外30多里远的镇上读初中起,就有了逛书店的嗜好。逛而没钱买,心里不免痒痒的,仍不舍恹恹而去。工作后有了收入才真正开始有目的地买书。年轻时常迷失于书山书海,书店书市书摊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时是去选购“正经书”,更多的时候是在那儿闲逛。凭借与卖书人混得滚瓜烂熟的“常客”的便利关系,被特许钻进柜台里“蹭读”是常有的惬意事儿。从那时到现在,一晃竟半个世纪了。我没统计过自己买过多少书,书房里大概有两三千册吧,并不多。我不懂得什么考究的版本,没有线装书,没有稀世珍本古籍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书没有价值,这种价值是无法用世俗的数字来计算的。我的这些书与我的人生相关,里面蕴含着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情感、我的努力。所以,我敝帚自珍,视它们为我相依为命之最爱,每一本书都有一段难忘旅程和美好心境,都有我的回忆。
说起过去的书事,若是不曾经历,兴许连理解都不大容易。记得曾经为之兴奋过好些日子的“巨大”收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一则短消息在《光明日报》举办的全国短新闻竞赛中斩获一等奖得到600元奖金后,一次性如痴如狂买齐了四大古典名著,还依照身为书店掌柜的书友李传新兄开列的外国文学阅读指导经典作家书目,一股脑儿把《神曲》《忏悔录》《十日谈》《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堂吉诃德》等30多种多卷本、大部头,连同上海译文社1982年版27集《契诃夫小说选集》,也疯魔般一集不落地“席卷”到家。那时的占有欲高度膨胀,必欲得之而后快。觊觎许久的名著终于如愿以偿地真正属于我自己了,那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边、敦实的手感、诱人的墨香,怎能不让人幸福得直嘚瑟?我旋即悟出:买书不但要有兴致,还得有钱。可细细想来,此举与学者陈子善所著《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中郁达夫的诗句“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的况味不是颇有几分相仿吗?蓦然回首,那种怦然心动之感,绝非用语言形容得出。
我之好买书,完全是从所从事职业的阅读与写作需求以及个人喜好出发的,尤以专业书、工具书这些普通书居多。像1980年版22.2元的《辞海》、1992年版140元的《汉语大字典》、1989年版《全唐诗典故词典》上下卷及《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等典诠“砖头”,我一向视为工作必备之要籍,不惜代价“供”于书房,信手拈来,以备查考。还有就是一些业余消闲的读物,杂而零落。无非是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职业追求与人生阅历,“挑食式”咀嚼,构筑属于自己的阅读格局与线索,从而在普通的书里品尝出自己的意味来。即便所读过的一些东西有一天终会忘掉,但正是这个被遗忘的过程赋予了一个人的知识架构与举止涵养。
藏书家韦力先生说他最觉快乐的就是获得书的那个瞬间。我虽非藏家,亦沉浸并享受于这一过程。我依稀记得人文社1981年版全套16卷《鲁迅全集》精装本是在怎样的情状下买下的。当时我月工资50元,连续在书店徘徊两三天后还是咬了牙决意花40多元狠心拿下,这可是“豪举”,只是想不起来那个月三口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购买过不少学者、大家、名家的著述、散文随笔,如王蒙的《我的人生哲学》、南怀瑾的《谈历史与人生》及史铁生的《日常生命观》等,读这类书即使随手翻翻,内心也充满愉悦,常常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叹。我在六堰老虎沟路的旧书摊上也有过意外的收获。以10元钱淘得上海春明出版社1955年版《李杜诗选》、人文社1956年版《唐诗三百首》,都是竖排繁体字,从左往右翻,还有一本长篇叙事诗中译本《列宁》,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著,人文社1953年版,与我同龄。从封底加盖的印章看,这是从武汉市新华书店古旧书市流散至十堰的。凝视着封面上那种晦旧的仿佛落满世尘、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深的淡黄色,恍然如山河岁月的丰厚沉积,不禁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没能幸运地走进大学校园,种种困扰下选择了自修。我把所有规定的专业教科书从四处搜求回来,都翻烂了,每本书页面都有折皱,眉批、随记密密麻麻森林般,波浪线排山倒海。即使在现今偶尔浏览书柜里的《中国报刊史》《中外记者经验谈》《标题的艺术》及《苏联名记者写作经验谈》,我都会感慨它们引导我踏入专业领域,为我打开了通向专业之门,若干年后承业界前辈抬爱,其小传及代表作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乡土名记者的追求》一书。
每每有了新居,总会预留一个角落给书籍。我迄今搬过6次家,每次搬家最头疼最麻烦的事就是书的迁徙。最难忘在县城内的两次搬家,因相距不算远,在县师范学校执教的挚友张君治安为我解了难题:课余时间他带来班上几十名学生,每人怀抱几十册书不等,列队整齐匀速地穿街而行,那一刻几成小县城街头一景,引得路人纷纷驻足窃窃私语:“哇,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呀!”而20多年前从县城搬往十堰就“淘气”多了。我年过花甲的老岳父和舅舅两人耗费了好几天时间把书柜里的书小心翼翼搬出后,又找来废旧报纸用力打包扎裹成20多包沉甸甸的“书捆”并编上号。妻子雇了货运专车告假亲自押运而至,方顺利安顿到它们也算体面的“居所”。
有时整理书房或找什么书,也会莫名地想,我等凡俗之辈买这么多书能看完吗?其实我清楚,穷尽一生也看不完自己所有的书了。每每买书回来,有的只是一目十行地翻一下序言后记留下大致印象,然后就放进书柜等后来某个机缘巧合再被光顾到;有的甚至连封塑都没拆开便塞进了书柜,认真读过的实在太少。这对那些书无疑不公平,甚至是事实上的轻慢与亵渎;对自己也是悲哀之事,那么多好书,如果读过自己一定很“牛”了。但人生匆迫,可能并没有太多时间坐在那里读书。这似不要紧,大凡有个念想就好。一个人有了书房,就攫住了一辈子的念想,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世间几乎所有的难题和答案都已在书柜里了。我想,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即使读不完书房里那一本本已经打上了岁月底色的书,也要把每本书都轻轻摩挲一遍,感恩它们多年来不离不弃的陪伴,感恩它们给我温暖、勇气和力量。
书房里有不少师友的赠书。看到它们,我便想起前辈先生的鼓励关爱,同辈朋友的勤奋精进,年轻一辈的后生可畏。对他们的创作与学术成就虽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但对他们尊敬的感情却是诚挚而单纯的。君子之交,素交为上。素如花骨,淡如春风,赠书为证。
书源源而至,我始终不能成功地为它们分类并编出书目来,因而大多类别含混、五花八门,相互掺杂。但于凌乱中亦觉丰盈,仿佛一个驳杂、深厚的世界那般。正如有人说的,书房是一个迷宫,只有自己才熟悉那些秘密小径。满柜的书毫无章法更无体系而言,无论是当机立断还是反复踌躇而得,其间无不倾注了爱书人嗜书如笃几近蛀虫般贪婪的满腔心血与炽烈情怀,是名副其实的精神宝藏。明亮的玻璃门透露出五颜六色的书脊,赋予它面前的拥有者一种莫名的满足,抑或一种富有的感觉。
书房伴我度过了大半生,我的人生与书房已然融为了一体。阅读,注定是我生命中无法舍弃的执念。偶然间记起清人张潮的话来,有工夫读书谓之福,以学而述著谓之福。如此看来,我是双福齐修,也算“‘名’副其实”了。
作者地址:擂鼓台巷8号